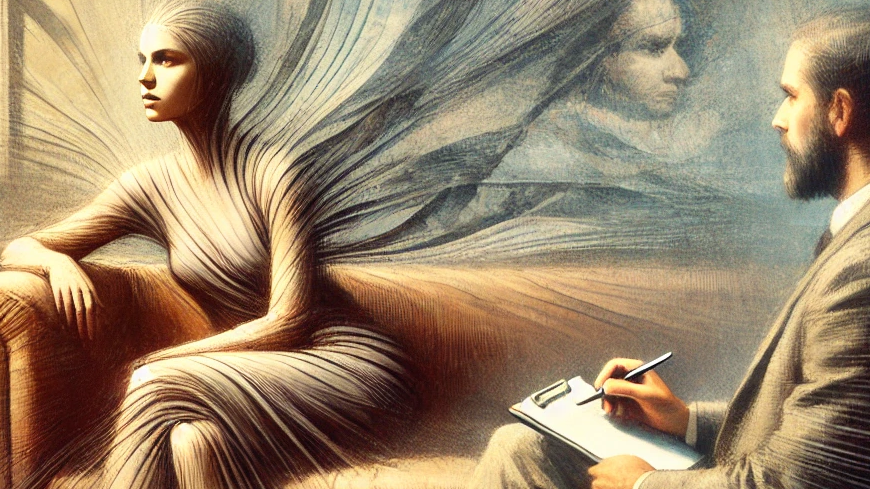作者:史蒂文.塔布林(Steven Tublin )博士
翻译: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
*本文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StevenTublinPhDSteven Tublin博士是WAWI(威廉.阿兰森.怀特学院)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纽约大学后期博士项目的教员,同时也是主体间心理学研究所的教员,拥有躯体体验法的实践资格证书,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方法,用于解决创伤。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当代精神分析技术、在临床研究中使用音乐与文学,以及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话题的文章。他的治疗方法结合了精神分析和躯体技术。作为教授、督导和临床工作者,Tublin博士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临床经验。
(本文获得作者本人授权翻译)关键词:音乐、个人风格、文学、详尽、探究
■ ■ ■在选择特定的音乐流派和文学作品时,患者有许多与精神分析探究相关的情绪活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控制自己的主观体验,寻求对特定情感的增强或麻木,促进理想自体状态的出现,或培养有价值的幻想。本文介绍了我使用沙利文式详尽探究的变体,来探索病人对音乐与文学的接受,并尝试将由此收集到的现象学和叙事学数据,与在当代精神分析探究中占核心地位的分析双方的材料进行结合。本文介绍了两个临床案例,展示了分析师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更深入地掌握博拉斯(Bollas,1992 年)所说的病人的 "个人风格"。
有四位几乎被我遗忘的高中同学,通过Facebook神奇地重新联系上,我们共进晚餐时,我发现自己在褪色封套中翻找 20 世纪 70 年代的唱片,那些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听过无数次的并不那么动听的唱片。把唱针放到老旧的黑胶唱片上,这个简单得近乎 "鲁迪特式 "(译者注:反对改进工作方法或技术变革的人)的举动,却让我在怀旧的温柔安抚中露出了苦涩的笑容。那个时代独特的声音——音乐本身,以及作为媒介遗迹的跳音、噼啪声和嘶嘶声——唤起了我对旧相识、令人生厌的旧时尚、海滩夏日强烈得泛黄的日光,以及年轻时的自己的回忆,年轻时的我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此时戴着耳机的我正在回忆过去的他。
我想知道,当我的一些同龄人——朋友、我尊敬和崇拜的人——陶醉于这些音乐中,感觉空洞、肤浅、冷漠、怪异、原始或干脆说是错误的音乐中时,我为何对这些唱片如此喜欢?博拉斯(Bollas,1992 年)曾写道,人类有能力赋予世界和世界中的事物以个人意义。他认为,这些客体,处于温尼科特式的 "中间空间(intermediate space)",即 "主体与客体相遇 "的区域(第 18 页)。在相遇的瞬间,个人改变了客体,同时也被客体所改变。在博拉斯看来,这个瞬间,就是 "个人风格"在所选择的物质客体中得到表达的时刻,这个“个人风格”,是先天的存在、记忆、渴望、习惯和文化秩序的独特组合。这是发生在思维领域之外的一种独特的个人思想变化。正如 Bollas 所说," 这里的目的不是创造意义或解释现实本身,而是与现实协商,以获得对释放了自我存在的客体的体验"(第 42 页)。这反映了一个人在与特定的、情感饱和的文化产品接触时,想要去意识到自身的某些本质的东西,也许是新生的、不成熟的东西。
在下文中,将介绍我尝试探索个人与特定形式的客体接触的方式,将重点关注文学和音乐作品——藉此了解个人风格的不同面向。我将介绍一种经过修改的沙利文式详细询问法,这种方法旨在全面了解患者的人际交往,针对患者在使用这类 "主观性客体"(Bollas, 1992, p. 20; Winnicott, 1953, 1967)时,如何产生出丰富的情感信息,这些信息在当代精神分析治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在以分析双方为中心的询问法中不易掌握的。这些信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人的感官体验,我主要依靠病人与音乐的接触;第二,叙事或文化维度,我从他们关于寻找小说和诗歌中的想象世界的叙述中所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旦成功,分析师就能凭直觉沉浸在患者的内心世界中,这就与通过语言表达唤起的内心世界截然不同。这两个艺术领域可以以三角方式结合在一起,将二元材料背景化,加深分析师对患者生活体验的理解。我将介绍两个临床片断,来呈现此类信息的使用,并强调了这种方法对衬托移情/反移情矩阵探索获得关系性材料的方式。
■■■探索音乐与文学
博拉斯 (1992)指出,主体与文化客体的有效相遇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心理,也取决于所寻找和接触的事物的特征。每种文化产品都有其内在的属性——博拉斯称之为 "利用结构(use-structure)"(第 33 页),这种属性可以用来阐释某些自体体验。面对近乎海量的文化产品,个体只追求那些能够实现其心理需要的文化产品。博拉斯描述了他年轻时对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热情,他发现这首曲子比巴赫的《B 小调弥撒曲》或灵魂乐先驱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早期作品(他也喜欢后者)更适合他当时的心理需求。
罗斯(Rose,1996 年,2004 年)撰写了大量关于精神分析对艺术、尤其是音乐的理解的文章,重点关注音乐通过复杂的、以身体反射的紧张和放松模式来影响情感体验的能力。罗斯(2004)借鉴了 朗格(Langer ,1942 年,1953 年)对推论象征(discursive symbols)和直觉象征(presentational symbols)的区分,前者的结构是为了传达普通语言中蕴含的形式逻辑关系,而后者则更适合代表他为了呼应米尔勒( Milner, 1957 年)而称之为的 "创造性或审美性思维"(第 98 页)。罗斯认为,朗格的美学理论建立在 "同源的(isomorphic) "原则之上,认为艺术源泉的形式会唤起听众或观众的一致的情感反应。他写道:"音乐的声音,就是感情的感觉,反映了感情的起伏、运动和静止、满足和变化"(Rose, 2004, p.97)。或者,正如朗格( Langer ,1953 年,第 27 页)所说的那样:我们称之为 "音乐 "的音调结构,与人类情感的形式,有着密切的逻辑相似性——增长和衰减的形式,流动和积蓄的形式,冲突和解决的形式,速度,停顿,强烈的兴奋,平静,或微妙的激活和梦幻般的失落——也许不是喜悦和悲伤,而是两者的升华——一切重要感受的伟大、短暂和消逝。这就是有知觉的模式或逻辑形式;而音乐的模式也是以纯粹的、有节奏的声音和寂静表现出来的。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语言。但是,临床工作者和理论家接触关系精神分析时,如果不将其视为一种有力的替代方案,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不需要任何支撑的取向,就会进入一个新的、不确定的精神分析世界。对他们来说,曾经为精神分析事业提供结构支持的技术及其原理,如今在建筑效果图上只是模糊的线条。学习关系精神分析的学生学会了许多理解病人经历的方法,但却很少得到他该说什么或如何表现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改变的方法。关系精神分析具有自发性、个人表达和独特的二元旅程的精神这些特征,但如果任其独立存在,结果证明不足以成为定义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础。
罗斯(Rose,2004 年)认为,这使得音乐成为精神分析交谈的很好的类比,而精神分析交谈既依赖于讨论的内容,也依赖于声音的体现和节奏(作者备注:Knoblauch (2000) 也阐述了类似的趋同性)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试图通过病人对特定直觉象征的喜好来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直觉象征是个人感受到的心理结构,但却不容易用普通语言表达的形式进行编码。
这样看来,分析师对患者所喜爱的音乐进行了解,似乎是进入自我私密体验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入口。通过聆听他人所追求的、表达其感受的音调和节奏,分析师或许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自己就是那个人,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驾驭着他们的生活。即使病人通常无法说出一首音乐所打动他的地方,有时分析师在聆听时也能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感受到病人的体验。
然而,直接了解他人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错觉。一个人即使听完全相同的音乐,也不可能真正以某种原始的、未改变的形式听到与别人所听到的相同的音乐。聆听者的心理会对干扰创造个人音乐/情感体验的过程:注意力的方向和强度、方向性和层次感的组织,以及这种刺激与听众内心生活的情感相结合的复杂方式,都会对体验产生影响。事实上,卡拉梅尔(Kramer ,2004 年)反对作曲家向听众传达单一的音乐 "信息 "这一观念。相反,他认为音乐会引起一系列不同的情感和审美反应,而这些反应是由不同的人/思想(如作曲家、表演者、制作人、录音师、听众)在最后的聆听时刻所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作者备注:这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篇幅不长的分析特定音乐作品特性的文献的前提相悖(A. Stein, 2004a, 2004b))。卡拉梅尔(Kramer ,1988 年,转引自 Kramer,2004 年)展示了听众在聆听同一首乐曲时的广泛的诠释范围。一位听众在描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称其为 "痛苦与悲叹的交响曲",而另一位听众则感到 "只有欢乐与生动"。还有人说它 "彻底的激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 "普通、温和的音乐"(第 40 页)。
这表明,为了让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对个人的直觉象征形成共同的理解, 必须通过反思性的语言表达来加以强化。分析师需要了解病人听到音乐时的感受、音乐让病人想起了什么、伴随着音乐的幻想(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等等。此外,对音乐意义的探索还包括聆听者赋予与音乐相关的富有生命力的全部联想。正如我在回忆中联想到的那样,音乐可以是一个赋予身份的领域,并将那些被遗忘、被忽视或被悄悄保护的记忆和自体的结构联系在一起。它承载着与时间、地点、群体成员和被遗忘的爱的连接。
对患者音乐体验的这种更丰富的理解,对分析过程大有裨益,因为它可以揭示出患者寻求特定听觉主观性客体的目的。聆听者积极地使用音乐,有时是精确地使用音乐,以唤起某些情感体验或避免其他情感体验。他们听音乐是为了感到欢快或沉浸在悲伤之中,是为了忘却或回忆,是为了感受力量的奔涌或是绝妙的细腻。他们也可以用音乐来分散注意力,或麻痹他们已经感受到的太多的情绪,把听音乐的行为当作一种麻醉剂,根据个人的心理,和需要被麻醉的确切痛苦,而量身定做。
对某些人来说,听音乐是进入某些自体状态的途径(Glennon, 2008),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受或想象自己与世界的互动,例如,战斗、喜悦或绝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自体状态对听众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被抛弃的恋人回到家中,在音乐中陷入悲伤或愤怒;或者健身狂人在凯旋的充满力量的歌声中编织她对胜利的幻想。然而,就像患者有时会忽略他们准确地一再重复的幻想内容一样(Person,1995 年),他们从未注意到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想象,他们也可能会忽略音乐的情感内涵,而这些音乐似乎在直觉上就适合他们。前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员的音乐资料库里藏有感伤的火炬歌曲(译者注:描述单恋感伤的流行歌曲),或者足球妈咪(译者注:带孩子训练的妈妈)在她的越野车里跟着 Metallica 一起尖叫,这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听觉体验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偏好。与他们可接受的自我概念不一致的情感,浸透了自我的方方面面,在这种私密的表达中寻到了出路。
那么,问题就不是 "这个人听的什么音乐?”相反,分析师应该问:"这种特定的音乐会唤起什么样的体验,这种体验又是如何在当下与这个人的心理和历史背景相契合的?”举例来说,为什么一个听众会选择沉浸在合唱团空灵的和声中,而另一个听众会选择慵懒的让人想起热带微风和带着律动与舞姿的巴西爵士乐?我们能从印度西塔琴的旋律中找到一种催人入眠的异国情调,而其他人听到的只是无形的嗡嗡声和叮当声?朋克音乐的好斗、新休闲音乐的反讽酷感、福音音乐的狂热宗教性、蓝草音乐的高亢孤寂——这些音乐流派都与寻求审美和情感刺激的心灵完美契合。特定流派的 “正确性 ”,部分源于音乐的神秘性,即声音的有序组合可以通过其运动(Sessions,1950 年)、紧张和释放(Rose,2004 年)的内涵,成为一种超验的体验生成器。但是,音乐与听众的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只有在特定个人的心理和生活背景下,才能实现其体验的价值。
因此,通过音乐来发现个人风格需要持续而专注的探究,积极关注细节,就像沙利文(Sullivan,1954 年)对人际关系形成结构的探究一样。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现在经常询问病人对音乐的兴趣,对于那些真正关心音乐的人,我会请他们为我制作一张 CD,作为 "他们生活的背景音乐"。我问他们,什么样的音乐最能向我表达他们的感受?(作者备注:有些读者可能认为这一请求打破了一般的诠释框架,因为在我的要求下,有了一个真实的物品交换,我邀请他们在疗程指定的空间/时间之外进行了隐性的接触。此外,我还了解了病人不在咨询室时的一些情况,而他们无法监控或立即回应我的反应。这些问题必须在移情性探究中加以解决,以确定它们对于关系的意义。此外,我们还认识到,这个选择本身,也会受到活跃于我们两个互动的人际张力的其他部分的影响。患者可能会选择音乐来试图打动、震撼、诱惑或排斥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移情性的弦外之音也值得进行特有的二元关系的探索。)有些患者觉得这个要求很清晰,于是开始着手捕捉他们的个人审美。而另一些患者则认为这项任务令人疑惑或毫无益处,进而表示反对(其中包括一位从事音乐行业的患者,他认为自己对当代家具的兴趣更能揭示问题,因此决定带来一本杂志剪报集)。
除了音乐内容本身,我的探究还涉及患者的聆听方式。他们是通过耳机播放音乐,还是像听觉壁纸一样使用音乐,作为在烹饪或上网时的背景音乐?音乐是否用于刺激肾上腺素,以促成极限的运动努力和身体宣泄?还是静静地聆听真正的音乐?当他们聆听时,是如何体验音乐的?是用身体还是用大脑去感受?音乐是否会唤起强烈的情感,如果是,患者寻求的是哪种情感状态,以及又是在什么时候?
正如音乐能表达其听众一样,对小说的接受和解读也能表达其读者。霍兰(Holland,1975 年)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文学研究者假定读者对特定文本有千篇一律的反应的想法,他提出了质疑。霍兰本人也是一位文学研究者,他对一群研究生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证研究,研究他们对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理解。霍兰毫不意外地发现,读者个性的各个方面,包括防御风格和特有的幻想,都会影响读者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体验和记忆。
我在这里介绍的临床方法将霍兰的观察延伸到了基本文学选择中的心理表达。性格不仅影响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影响他们的阅读内容。因此,我询问文学作品的选择和参与情况的方式类似于询问音乐的方式,即, "你读什么书,读的时候有什么体验?”与音乐一样,我也会询问患者的阅读习惯。他们是在深夜长时间阅读,还是在做其他事情的短暂间隙时间阅读?他们阅读是为了获得熟悉情节的安慰,还是为了邂逅奇闻趣事,是为了激发某种情感,还是为了抑制其他情感?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喜欢或排斥哪些人物?
对文学的探究可以进行类似于音乐的美学探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创意写作视为产生情感体验的语言艺术(Langer,1953 年),事实上,患者,尤其是那些热爱语言本身的患者,对阅读的这一方面充满热情。然而,书面文字的使用结构也允许探索明确的叙事成分。我将这方面的文学探究比作 "主题统觉测试"(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默里,1938 年),这是一种传统的评估工具,向病人展示一系列容易激发起感受的场景,并鼓励他们说出场景中描述的故事。我们可以认为,向患者询问他们自己的文学爱好与他们选择自己的卡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 TAT 一样,在询问文学作品的选择时,我也会询问患者对世界运行方式、道德秩序、权力分配、仪式和制度的假设。除了唤起特定的情绪和感觉之外,文学作品还允许读者选择一个暂时生活的世界,一个具有道德结构和风俗习惯的社会空间,其中有各种类型的人在独特的文化秩序中做着特定的事情。因此,文学作品的选择不仅告诉分析师,他的病人如何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包括他们想要进入什么样的想象中的文化空间。
就像对音乐的探究一样,问题是,什么样的思想能与什么样的想象空间产生共鸣,又是为什么?例如,唐-德里罗(译者注:Don DeLillo,美国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也是美国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叙述者、阐释者、批评者。)的阴郁和偏执如何与特定读者的历史和更广泛的心理背景相结合?追随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美国当代作家)冗长而琐碎的叙述和无穷无尽的脚注有着什么样的情感目的?读者从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笔下的法国、埃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的侦探小说或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短篇小说的蓝领极简主义中获得了什么?
音乐和文学可以产生不同的数据,当这些数据与以人际关系为导向的材料相结合时,就能产生对患者心理和生活方式的丰富理解。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介绍两个临床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我利用这些资源收集了现象学和文化资料,这些资料有力地补充了每个治疗的核心——人际间关系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