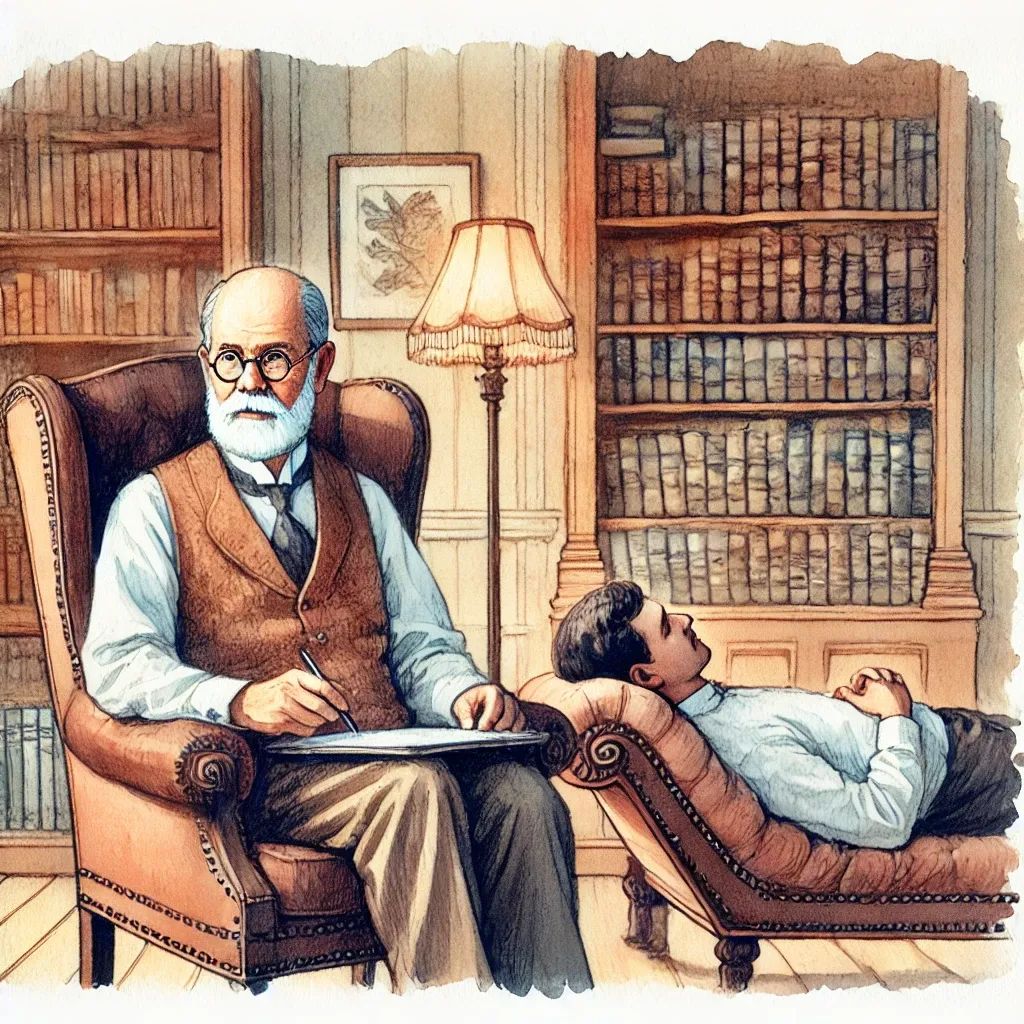作者:Steven Tublin PhD
翻译:刘琼(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学员)校对: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
*本文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Steven Tublin PhD
Tublin博士是WAWI(威廉.阿兰森.怀特学院)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纽约大学后期博士项目的教员,同时也是主体间心理学研究所的教员,拥有躯体体验法的实践资格证书,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方法,用于解决创伤。
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当代精神分析技术、在临床研究中使用音乐与文学,以及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话题的文章。他的治疗方法结合了精神分析和躯体技术。作为教授、督导和临床医生,Tublin博士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临床经验。
关键词: 关系, 精神分析, 历史, 政治, 异议, 革命, 压制。
此次研讨会探讨了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在历史、理论和政治上的联系,并重新回顾了这些竞争思想派别之间的激烈内部冲突的动荡历史。虽然这里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为了讨论这两个学派之间的理论联系,但它们也记录了一段不幸的历史:在面对充满活力的异议和创造力时,学术机构的正统思想一再变得僵化。尽管当前的精神分析讨论相对没有这种无益的冲突,但可以预见,随着关系学派逐渐获得某种既定的合法地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自身重大的理论挑战,人们或许可以预见到这样的冲突轮回,但希望能够避免。
在此次研讨会一开始,Donnel Stern在他为大会撰写的文献中基本上就放弃了尝试明确界定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之间联系的努力。“人际理论和关系理论,”他指出,“是概念和临床上的大伞,为同行者提供庇护。”因此,它们事实上是难以真正“解开”的。的确,Ehrenberg 在其为研讨会撰写的文章中提到,自人际和关系理论各自出现以来,两个领域内一直包含着大量的不同意见。如今,要提炼出这些一直是广泛、多样且有时互不兼容的思想体系的精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要定义它们之间的关联,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想,研讨会标题中设定的乐观目标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不过,后面五篇文章的尝试至少解决了两个不同且及时的目标,其中一个或许尤为紧迫。首先,这些文章汇集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当代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论和技术领域。关系精神分析现在在精神分析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已经从一个宽泛、定义松散的方向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学派。关系精神分析从许多来源中汲取灵感,尽管那些来源的重要性可能因人而异(Mitchell, 1998; Frankel, 1998; Hirsch, 1998)。人际精神分析,从上世纪中叶的创始人到如今,仍然有自认仅作为纯粹人际主义者存在的少数作者群体,一直是整个关系理论运动的核心灵感来源——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最核心的灵感来源。接下来的文章展示了这两个思想体系间联系的复杂性,以及要分离出两者间任何线性联结的困难。
其次,也许更为紧迫的动机则回到了你问的是谁这个问题上。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的故事,不仅是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这一故事在接下来五篇文章中的四篇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只有Crastnopol在她那简明的、通过人际和关系的思维来分析自体演变的论述中,完全停留在理论范畴内。就像接下来的文章中所述,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机构之间斗争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领袖、教师和叛逆者的故事。随着关系学派逐渐确立,一些人开始担心,在学院的记忆中,人际理论和人际主义者在建立关系精神分析中的作用会逐渐消失。因此,在这里的一些讨论中,我们也能听到关于政治身份和遗产的情感问题。这使得研讨会的讨论呈现出另一种意义。讨论的参与者作为部落长老,重温了一段创伤性和奠基性的历史,以适当的方式纪念那些通过战斗在新的精神分析世界中为我们开辟疆土的人们的贡献和牺牲。他们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如何从荒漠中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我们的。”
这个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取决于读者的视角。人们很容易将其看作开放性、创造力和人性尊严战胜僵化的制度正统的英雄事迹。然而,这些论文中出现的另一个或许更具说服力的叙事是,无论“谁”掌握权力,僵化的固执和对反对意见的压制总是反复上演。一次又一次,人们会看到顽固与创新碰撞,并压制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反对声音。
反派角色随着每一章的展开而变化。二十世纪中期的弗洛伊德学派反对各种异端学说,包括最初的人际关系理论学派或“文化”精神分析师(参考Levenson在本期文章中的讨论)的新奇想法,这些学者后来创立了怀特学院。但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精神病学家排挤心理学家(这一争斗,在某些地方有类似关于硕士学位候选人的争议),男性拒绝让女性进入这个领域,另外还有一个带有黑暗但具启示意义的讽刺——一代人际关系学派的学者牢牢控制着他们自己的机构,却排斥那些希望将客体关系特征整合到人际关系理论中的思想家。这种分歧和最终的决裂促成了后来被称为关系学派的发展。
我猜想,这个故事对不同代际的分析学家来说会有着不同的共鸣。对于那些一次又一次参与或近距离目睹各种机构激烈冲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叙事,其中充满了相当多的情感。在随后的几代人中,确实有些人将这段历史视为自己的历史,并与长辈们有同样强烈的感受。但也有很多最近才成为分析师的人,对这段历史已经失去了直接性。它的意义更多在于如何启发当前的理解。在后现代时代,精神分析临床医生获得的指导也少了很多。那些相互冲突的诠释方案为从业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选择,用以理解病人的生活、临床遭遇和治疗变化的过程。对于在这个多样化和智识多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要找到清晰的方向变得很难。厘清,或者只是人际关系和关系理论中错综复杂中能定位,会让许多新近加入者对理论区分和临床选项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应该如何对待病人以及这么做的原因。对他们来说,纪念过去的英雄和不公则显得没那么重要。
我自己的观点处于两者之间:与实际的争斗隔了一层、同时距离又足够引起个人的共鸣。从一部分脱开的立场来看, 我倾向于以一种可能并不是与会的嘉宾们所意图的方式考虑这些被定义的故事的意义。对我来说,(精神分析)历史上不断的革命、精简和压制的故事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的重要事件,更是对这一领域的性质及未来可能发生类似裂痕的黑暗警告。
当前的精神分析阶段没有那种曾导致人际和关系学派出现的激烈斗争。我们不缺乏需要考虑的想法,而且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发展和扩展这些想法的任务正在进行。即便是对当代冲突理论的反对——这是人际和关系精神分析历史上的常态——也已变得温和,变成了一种礼貌且合作的努力。许多弗洛伊德学派的追随者已经接受了作为关系理论基础的双人(双主体)立场。如果有敌人,那也是外部的,主要是针对精神分析治疗整体怀有敌意的各种管理式医疗运营。
但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借鉴,那么这一相对和平的时期是有时限的。关系精神分析——在这里我使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自认是关系学派或人际/关系分析的广大的分析家群体——无论其作为一种反抗和革命性替代的历史,现在都绝非边缘学派。它不再仅仅是一套思想或一种治疗方法,而且已经积累了所有确立其合法地位的装备。现在这已经是一个拥有自己期刊、培训机构、不同性别的领袖导师、专业组织以及会议的社群。通过这些制度性权力工具,关系正统性的出现(无论是隐晦的还是明显的)还会远吗?
目前还没有组织化的反对力量来挑战关系立场的基本前提,但同样的,如果历史有任何可借鉴之处,我们必须预计某个时刻会出现这样的反对力量。事实上,这样的反对力量应该存在,否则就会陷入一种静态的自满,只是旧观念的循环再现而已,而非真正的学术交流。问题在于,当这种反对力量出现时,是否会被接纳并可能进行辩论,但最终作为一种挑战而受到欢迎,从而促进更好的理论和实践。又还是说,内部挑战的出现又会导致压制和革出教门?可悲的是,精神分析的历史并没有表明对新事物会以积极健康的态度接纳(例如,Eisold,1998年)。
本次研讨会对历史的重温和审视,虽然纪念和反思了塑造当代精神分析中人际关系和关系派系的创伤性历史,同时也警示我们,随着激烈的反对意见不可避免地到来,我们可能会同样面临的潜在的危机。
参考文献:
Eisold, K. ( 1998), The splitting of the New York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analytic authority. Int. J. Psycho-Anal., 79: 871-886. Frankel, J. ( 1998), Are interpersonal and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the same? Contemp. Psychoanal., 34: 485-500. Hirsch, I. ( 1998), Further thoughts about interpersonal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Reply to Jay Frankel. Contemp. Psychoanal., 34: 501-538. Mitchell, S. ( 1999), Letter to the editor. Contemp. Psychoanal., 35: 355-359.